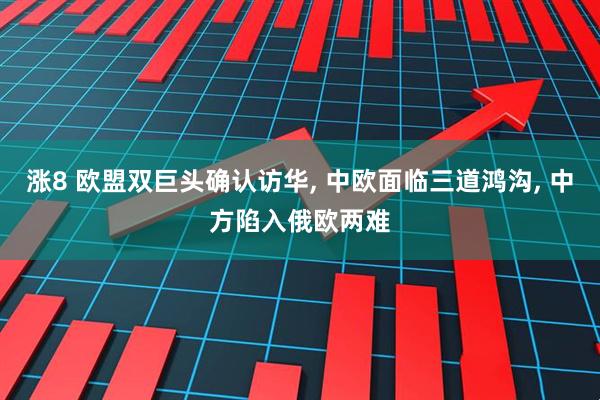
各位朋友涨8,大家好。
本周至关重要,除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将继续微妙地推进以外,中欧峰会也将定于24号在北京举行。
7月21日上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宣布,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也就是欧洲的双巨头将于24日访问中国。

坦率地说,在峰会召开前,大家对于中欧今年的年度峰会能否取得成果和突破的信心依然不足。尤其在当前美国对中国和欧洲施加贸易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和欧洲能否联手,至少像过去一样采取策略性的合作,依然是个未知数。
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上升到了战略层面。
大家是否感觉到其中的诡异和荒唐?因为中欧双方都承受着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压力不用说,一直都存在,并且最近双方正在进行非常艰难的博弈。
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对欧洲也开始施加强硬态度。由于欧洲在部分问题上的不妥协,特朗普在恼羞成怒之下,宣布将对欧洲增加高达30%的关税。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中国依然强硬,这显示出了内在逻辑的荒唐,或至少是不合理之处。
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俄罗斯。
因此,当我们展开话题时,会发现其实我们涉及到了包含中美欧俄这个复杂的大三角关系。
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过去二三十年我们曾经历过两种不同的三角关系。一种是根据经济关系来划分,即中美欧;另一种则是根据政治关系来界定,即中美俄。
尽管俄罗斯并非经济强国,但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无疑是一个政治强国。
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虽然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打得非常艰难,但明眼人都知道,无论从未来的政治军事实力或者影响力而言,还是从威权的强人政治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谁能够占上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依然在世界政治三角关系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欧洲涨8,长期以来被称作“经济巨人、政治侏儒或矮子”,始终未能充分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乃至在疫情爆发前,欧洲与中国在进行双边战略磋商的过程中,尽管形势逐渐变得艰难,但至少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双方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合作。
然而,三年半后的今天,当欧洲和中国同时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时,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却依然强硬。
坦率地说,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策略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战略课题。
我们先回到策略层面的讨论。
目前看来,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双边会晤似乎已遥遥无期。
7月20日,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公开表示,美俄领导人的会晤不是在短期之内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中间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
他还否认了外媒传闻,即9月中美俄同台,佩斯科夫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实际上与我最初的预测一致。鉴于目前的情况,美俄峰会似乎遥遥无期,而中欧峰会已经开始进行。
同时,关于中美峰会也有了最新消息。
据港媒透露,今年的APEC峰会将于11月在韩国举行,届时中美峰会要么在峰会期间举行,要么在峰会之前举行。如果是在此之前举行,那可能就是特朗普顺访。
目前来看,无论哪种情况,都还无法确定。
如果特朗普决定来访,那么8月12日将是一个关键的日期。中美两国在5月12日推迟90天的关税缓和期内,一定要达成一个协议,或者再延期90天。

不过我想,即便再推迟90天,特朗普来访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贸易战博弈仍在继续。
唯一可能性是在8月12日或之后涨8,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顺利达成协议。尽管目前看来困难重重,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所以,8月12日之后再顺延90天的可能性更大。
坦率地讲,我认为延期也是一件好事。那至少说明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关系破裂,因为达成协议需要一些重大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双方必须从之前无休止的博弈中,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进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美国目前正在与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等全球多个国家进行贸易谈判,但这些谈判的顺利程度,均不及其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
这表明,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处境最为舒服的国家之一。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表象,背后实则是两国在谈判中通过激烈的竞争和博弈来争取优势。具体表现为中国利用稀土作为杠杆,卡美国的脖子;而美国则凭借高科技芯片出口,卡住中国的脖子。
前几天我多次提到黄仁勋,他作为英伟达的总裁,一直在中美两国之间游刃有余地游走。
一方面,黄仁勋的角色既值得高度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适度看待,不能过分高估黄仁勋或英伟达的作用。
毕竟中美之间的这种近身肉搏,双方在被对方卡住脖子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自退让,其实质是脆弱的,是无奈的选择。因此,人们不应盲目对中美关系抱有战略性的、结构性的信心。
不过,中美关系的任何缓和对于中国经济结构尚未完全转型、仍高度依赖世界的现状来说,都是一种暂时的缓冲。但这种脆弱且短暂的缓和,需要得到其他地方战略性的支持和后援。
说到战略上的支持和后援,它是来自欧洲还是俄罗斯?对中国而言,目前大概只有两种选择。当然,日韩两国相对来说是比较次要的,伊朗、朝鲜、巴基斯坦等亦是如此。
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无论是结构性、战略性,还是策略性、阶段性的博弈,它都是一种近身肉搏的关系,都需要背后有支持,或者至少要有人周旋,无论是向东还是向西的国家。
向东,那就是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之下的其他一些国家;向西,则是欧盟以及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
有关这个问题,其重要程度不亚于1969年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即同时与美国、欧洲及苏联为敌,还是在与苏联交恶的同时,远交近攻,联合美国。
最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就是联合尼克松,这不仅促成了中美关系暂时的正常化,而且为1972年至1979年的七年期间,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对峙带来了较为有利的战略态势。

此外,这七年的积累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如果没有1972年至1979年这七年的西方资源积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能不会如此顺利。这一成就,与其说是第二代领导人的功劳,不如说是第一代领导人打下的坚实基础。
另一个能够类比的“十字路口”,是在1992年中国果断地实行市场经济,这实际上也是向东走向西走的问题。
如今,中国再次面临这样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其实早已存在,只不过过去中欧之间的矛盾并未凸显。
说实在,中欧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
然而,当双方共同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时,中欧两家都成为了牺牲者,结果这两个牺牲者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
首先,这其中有许多是欧洲的问题,包括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这一直是困扰双方的一大难题。
其次,中国电动车市场的大幅增长,大举倾向欧洲市场,给他们带来了骚动和不安,这也是欧洲人格局的问题。
最后,是来自俄乌战争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欧盟对此并未买账,反而更加坚信中国与俄罗斯是一伙的。
从我们的角度看,这完全是一种误读。
从中国背后的战略角度来说,欧洲对中国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中国未来国运的发展重要性到底有多大?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前人所言,中国的国防是海防还是塞防?清末的中国,由于资源有限,捉襟见肘,但坦率地讲,今天的中国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它依然是中国一个长期的战略伙伴,无论是在地缘战略上还是其他方面,双方能够共同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正面挑战。
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思考是否要战略性改善与欧洲的关系。
在过去,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由于俄乌问题,欧俄直接对抗,也就是中国两个可以依靠的伙伴直接对抗,这使得中国陷入两难的境地。
然而,我认为,从战略上来看,这并非是不可解之局,中国要想解决这个困局,就必须要从国家的民族、历史上进行长远的考虑,这样中国就完全可以解开这个困局。
因此,我刚才列举了一些的比喻,无论是清末的海防与塞防问题、1969年中国领导人的选择,还是1992年果断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尽管时空环境、议题和本质各不相同涨8,但从战略谋略的角度来看,都可以给予我们不少战略上的启示。
垒富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